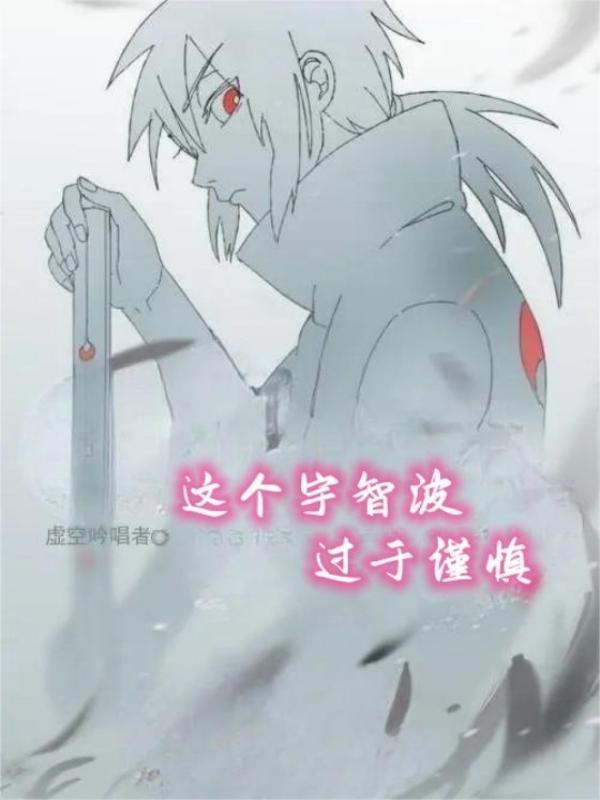新纳兰小说>一百首诗词 > 第70章 李康运命论(第4页)
第70章 李康运命论(第4页)
译:姜太公本是渭水岸边的贫贱老人,却在周朝被尊为尚父。
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
译:百里奚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他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在秦国才有才能。
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译:张良得到黄石公授予的兵书,诵读《三略》的学说,以此游说群雄,他的主张,就像把水泼向石头,没有人接受;等到他遇到汉高祖,他的主张,就像把石头投入水中,没有人违抗。
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
译:并非张良在陈涉、项羽面前拙于言辞,而在沛公面前善于言辞。然而张良的言论是一样的,为什么有时被接受有时被拒绝呢?这种接受与拒绝的原因,是神明的旨意。
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
译:所以伊尹、姜太公、百里奚、张良这四位贤者,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图箓上,他们的事迹顺应了天命与人事,这难道能用贤愚来衡量吗?
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
译:孔子说:“自身保持清明,气志就如同神明。当嗜欲将要到来时,必定会先有征兆。就像天降及时雨,山川会先出现云雾。”《诗经》说:“巍峨的山岳降下神灵,诞生了甫侯和申伯;正是因为有申伯和甫侯,他们才成为周朝的栋梁。”这说的就是命运啊。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
译:岂止是兴盛的君主如此,导致国家混乱灭亡的君主也是这样。
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于夏庭。
译:周幽王被褒姒迷惑,灾祸的征兆在夏朝宫廷就已出现。
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于社宫。
译:曹伯阳得到公孙强,征兆在社宫显现。
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
译:叔孙豹亲近竖牛,灾祸在庚宗酿成。
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译:吉凶成败,都按照一定的气数到来。它们都是不用刻意追求就能自然契合,不用别人介绍就能自然亲密的。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
译:从前,圣人接受河图洛书的启示说:“凭借文德受命的,七九之数时就会衰落;凭借武力兴起的,六八之数时就会谋划变革。”
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译:等到周成王在郏鄏定都,占卜得知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的命令。
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
译:所以从周幽王、周厉王时期开始,周朝的政治制度就严重败坏,春秋五霸之后,礼乐制度逐渐衰败。
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
译:文化浅薄的弊端,在周灵王、周景王时逐渐显现;诡辩欺诈的风气,在战国时期形成。
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
译:严刑峻法的极致,在秦朝积累;文章辞藻的尊贵,被汉高祖弃置。
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译:即使是孔子这样的至圣之人,颜回、冉求这样的大贤之人,在礼仪规范中相互礼让,在洙水、泗水之上和颜悦色地讲学,也不能阻止衰败的开端;孟轲、荀况效法二位圣人,遵循正道,也不能挽救末世的颓势,天下最终陷入混乱而无法挽救。
此所谓命也。岂惟一世哉?
译:这就是所说的命运啊。难道仅仅这一个时代是这样吗?
且夫天下事不可胜数,狐疑犹豫,当断不断,必有后祸。
译:况且天下的事情数不胜数,遇事犹豫不决,该决断的时候不决断,必定会留下后患。
故知者审于量主而进,不达者追于成名而退。
译:所以明智的人审慎地衡量君主然后决定是否进取,不明事理的人追求成名而盲目行动然后才知退避。
若夫吕尚之遇文王,宁戚之迕桓公,或投己于鼎镬,或释褐于版筑,去之则神罢气沮,就之则成王定霸,然而二子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乃得荐达哉?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译:像吕尚遇到周文王,宁戚冒犯齐桓公,他们有的甘愿赴死,有的从筑墙的劳役中被起用,离开这些君主就会精神萎靡、志气沮丧,追随这些君主就能成就王业、奠定霸业。然而这两个人,难道是一向在朝廷为官,借助身边人的赞誉,然后才得以被举荐显达的吗?
精诚感于神明,忠义服于邻国,岂借问于乡闾,比誉于品藻,然后乃光扬哉?
译:他们的精诚感动了神明,他们的忠义使邻国敬服,难道是借助乡人的称赞,通过品评者的赞誉,然后才声名远扬的吗?
及至从仕也,趋舍不合,言语相违,俯仰异趣,功业不建,有自来矣。
译:等到他们入朝为官,与君主取舍不合,言语相悖,志向不同,功业无法建立,这是有原因的。
故僚相视而笑,朋执摇头,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岂可得哉?
译:所以同僚们相视苦笑,朋友们摇头叹息,想要探求其中的原因,又怎么能得到呢?
夫疾风劲草,岁寒松柏,事患难然后知君子之不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