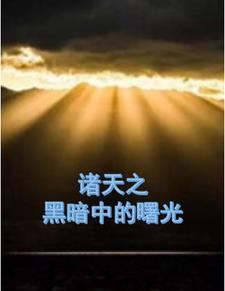新纳兰小说>朕怀了敌国质子的崽免费阅读 > 第26章(第1页)
第26章(第1页)
段晏在竹意堂等到天色渐晚,派去御书房请宁诩的宫人才苦着脸回来。
“公子,陛下他不来啊。”宫人忧愁道:“只是让内务司待会给我们多送些炭火,来驱散殿内的寒意。”
不等段晏开口,他又急切地说:“不过公子,奴才刚从御书房离开的时候,瞧见那王公子冒雪求见,陛下竟然也让他进去了……”
此话一出,旁边的宫人们都悄悄抬眼去看段晏脸上的神色。
要是、要是他们的段侍君也能如从前一般舍下面子,去御书房门口堵陛下几次,说不定就能重获宠爱了呢?
常言道旧情难忘,段侍君长得这样好,稍微软下脾气求一求陛下,什么事不能成啊!
段晏似是察觉到周围宫人们的心思,却依旧冷淡道:“你再去一趟,就说我风寒未愈,头疼不已,让陛下务必过来看一看。”
领了吩咐的人苦着一张脸又出去了。
段晏转身往寝殿内走,将一众形形色色的不满目光抛在身后。
……他如今已不愿意戴上伪装的面具,在宁诩面前表演出一副温柔大度的模样来了。
现在的他,要是去了御书房,对上那日日缠着宁诩的王知治,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或许出手杀了那姓王的也说不定。
段晏拧着眉心,想。
他回到寝殿,关上门,在榻沿上静静坐下。
冬日的天色暗得早,屋里却没有点烛火,青年默默待在冷如冰窖的殿内,等着看宁诩究竟会不会过来。
也等着看,在宁诩心里,对他究竟是只有抵触和防备,还是残留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情意。
*
御书房内,宁诩长长叹了一口气。
宋公公也跟着叹了口气,无奈道:“陛下,竹意堂的宫人又回来了,候在殿外,说段侍君受风头疼,整个人冷得和块冰似的,一定要让您过去探望呢。”
宁诩抬了下脸,还没开口,就听见旁边的王知治抢先说:
“宋公公,您这就不对了,陛下已经拒绝过一次,怎么还让那竹意堂的过来?几次三番地过来打搅,是要违抗旨意吗?”
宋公公愣了下,赔笑道:“王公子,奴才也只是尽自己的本分,万一段侍君真有什么好歹……”
王知治:“头疼脑热就去请御医,雪天畏寒就找内务司,找陛下做什么?宋公公,我看你是昏了头了。”
听见他的前半句,宁诩本来还那么几分认同,但又听见王知治叱骂宋公公,不由得蹙眉,不高兴道:
“宋公公是朕的御前大太监,当然知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教训朕的宫人干什么?”
宋公公每日勤勤恳恳做事,从无丝毫怨言,是老黄牛中的战斗牛,宁诩都看在眼里。
他不允许随随便便来一个外人都能骂宋公公!
王知治怔了一下,显然没料到宁诩还会出言维护一个奴才,忙解释:“陛下,臣也是想着您,那段晏屡次遣人过来打扰您,赶也赶不走,不是更让陛下烦恼吗?”
宁诩面无表情道:“哦,可是你也硬要赖在御书房里,朕几次让你回去,你也不回去啊。这么说来,你岂不也是违抗圣旨了?”
今天王知治带着他南方老家的瓜果来,说要给宁诩尝尝。
在门外站了小半个时辰,宁诩担心他被冻傻了,只好把人放进御书房。
结果王知治一来就不走了,殷勤给瓜果剥皮切块,端到宁诩跟前,期待地请他品尝。
一个多时辰后,宁诩的肚子里装了一堆东西,饱得直打嗝,连晚膳也吃不下了。
听见他的话,王知治抿了下唇,低声说:“臣从未有如此亲近陛下的时光,忍不住想再将这时光留得久一些,陛下却这样责怪臣,让臣好生难堪……”
态度是低声下气的,回去的话是只字不提的。
宁诩有点麻木了。
今夜夏潋出宫去察看京郊的水利工程,还没回来,这御书房里只剩他和一个王知治。
他实在不想再吃王知治剥的果子了……
思及此,宁诩开了口:“宋公公,竹意堂的宫人还在外面吗?”
宋公公说:“在,都跪了一会儿了。”
宁诩正从御案后起身,闻言忍不住道:“地上都是雪水,怎么能跪着?膝盖还要不要了。”
他出了御书房,看看那愁云满面的竹意堂宫人,说:“起来吧,和朕说一说,段侍君究竟怎么了?”
不会又是诓他的吧?
宫人战战兢兢地开始瞎编:“公子……身患旧疾,每逢入冬就会犯头疼,在殿中晕了好几次,脸色苍白,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宁诩一听,不得了啊,这恐怕是脑溢血了,赶紧派太医署的人过去治一治,迟了怕是只能把段晏横着抬出来了。
结果见他要下令让御医过去,宫人又慌张道:“陛、陛下,我们公子的症状没那么严重,用不着御医的,只要……只要陛下过去看一看,抱着哄一哄,最好还能留宿一晚,就就就没事了!”
宋公公及其他人:“……”
宁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