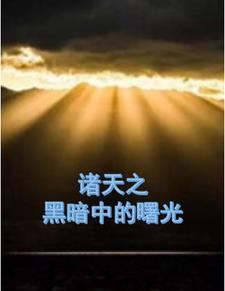新纳兰小说>女扮男装被发现 > 第4章 殿下这个很好吃的(第1页)
第4章 殿下这个很好吃的(第1页)
屋漏偏逢连夜雨,初春的雨水毫无预兆,密密麻麻地落下。
国子监学堂屋檐宽大,可风裹挟着雨水依旧砸在了江昭身上。
细微的湿意打湿衣襟,顺着脖颈钻进里衣,风一吹,寒意瞬间渗进骨髓。
江昭缩了缩脖子,白皙的小脸鼻子被冻的通红。
只恨方才没趁着慌乱,多踹江时叙几脚。
按理讲,迟到要在外头罚站半个时辰,江昭抬头看了看天,这雨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估计还有得冻的。
风吹动书院的窗子出扑扑的声音,江昭瘦小的身板像是能被风刮走。
江时叙透过窗子,看着这一幕,眉心紧蹙。
“这傻子到了上课时辰,乱跑什么?”
看着江昭好似摇摇欲坠的背影,他脸上有过一丝古怪,可转瞬又觉得荒谬,他没事担心江昭干嘛?
倒是一旁的沈青词一双狐狸眼微微上挑,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外头这雨没个一时半会怕是停不了,也是让江昭这傻子吃了些苦头。”
按理来说,沈青词该唤江昭一声“表弟”,但他向来不将江昭放在眼里。
江昭乞儿出身,行为粗鄙,更时常装作可怜让自己屡屡受罚。
想起年前,他和江时叙见入冬后裹得跟个鹌鹑似的江昭,心中满是不屑,便起了捉弄之意,将那残雪塞进江昭衣襟。
这本是少年间的玩闹,但事情却不知怎么的传进沈家父母耳朵里,沈青词当晚便被家法伺候,被关进祠堂跪了三天三夜。
他大病一场后再回书院,江昭倒是活蹦乱跳,无事生。
果真是心机深沉。
沈青词看着窗外的江昭,眼中划过一丝狠意。
既然年前的残雪江昭能受得住,那下次就换国子监那一湖刺骨的冷池试试。
他非得让江昭尝到些苦头。
江时叙握着笔的手紧了紧,别过脸去。
“这傻子活该。”
外头的雨越下越大,终是夫子看不下去了,走到后门挥手,朝江昭挥了挥手。
夫子年迈,满是褶皱的手抚了抚胡子,看着江昭站在外头呆的模样无奈的摇了摇头。
本就是痴儿,何必如此严厉。
“进来吧,下次莫要再犯。”
江昭听见声音,连忙朝着夫子点头道谢。
“多谢夫子,学生知道了。”
比起屋外的冷,屋里就暖和多了,四周烧着上好的银丝碳,每个座位旁还有放置着漆铜炉子,感受不到一丝寒意。
江昭朝自己的位置走去,她的衣摆和鞋履被打湿,在地上留下一道水痕。
江凌言一双琉璃似的眼睛淡淡扫过江昭袖口。
她半截袖子被全然打湿,葱白的指尖被冻的通红,略微有些狼狈。
夫子轻咳一声,示意众人目光再次回到书卷。
江凌言眸中无波无澜,仿佛刚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江昭个头不高,被安排在第一排。
她坐下后,也没着急去拿书本,而是先把桌旁放置的小炉子放在桌前,开始烤起火来。
江昭满身狼狈,束起的冠有些散落,几根丝遮挡在额前,让人看不清的眼底的神色。
还好夏云给她穿得足够多,除了被湖水打湿的衣袖,其他地方并没有浸湿里面,把手烤热了,倒也不会太冷。
江昭搓了搓手,被冻到无知觉的手心有了些暖意。
满京城都知江三公子痴傻,江家父母花了好大力气才将江昭送入国子监。
知道江昭的情况,夫子对她的行为也是视而不见。
国子监一堂课便是一个时辰,等讲课结束,江昭的袖子都烤干了。
江时叙身形高大,他坐在后排,随意拿了张宣纸揉卷成团,朝江昭扔过去,刚好砸在江昭头上。
江昭不是第一次被砸了头,她扭头一看,果真又是江时叙。
“你这方才跑哪去了?”
江昭心中憋着气,不愿理会他。
若不是江时叙克扣她早膳,她便不会去采摘黄芝,也不会被晏为卿抓住,更不会因为迟到被罚站。
她抿了抿嘴,在袖中翻找。
这边,江时叙见江昭没应,干脆起身来到江昭桌前,刚好看到江昭拿出最后两根黄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