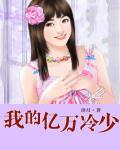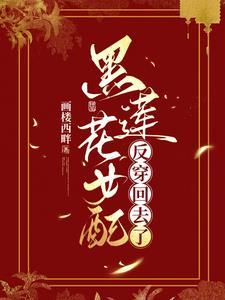新纳兰小说>农家幼崽竹马日常by秃了 > 第95章 农事官(第3页)
第95章 农事官(第3页)
就算走近听到不是,还得借机骂几句他们傻,他们怎么傻了?
明明是章家真倒霉,这事情落谁身上不倒霉?都是种庄稼的,还允许他们心疼了?
说来说去还是里正生疯骂人哩。
谁叫郑秋菊肚子不争气。
和张书生成婚六七年了,肚子一直没动静。最近张书生要纳妾,说是一天去同窗家吃酒,他吃多了,同窗妹妹照顾,阴差阳错有了关系。
现在要对人家负责,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这样把人娶回来了。虽然是说纳妾,那聘礼一对对的,足足用了十几个人去挑箩筐的。
这可不是打郑里正的脸,但这事情他就是里正也没法子说。毕竟谁叫他女儿肚子不争气。
村里的家长里短就是这些,聚在一起少不得说道。所以郑里正看见人聚就脾气不好要骂人。
村民也只当里正找他们不痛快骂他们傻子。
村民回到家里,就学着那出五十文钱的村民说章家的事情,结果把人想坏的不止他一人,瞬间觉得平衡不少,只把这个事儿当个乐子。
于是家里走亲戚、回村走娘家的媳妇儿,都拿章家这事儿当乐子逗人好不有趣。
渐渐的,整个镇子上的人都知道章家姜坏了,宁愿烧了也不卖,就是地里有点风险的也不坑人骗钱,这口碑那是响当当的好。
一传十十传百,没人不知道的。
几年后如里正所想,随着姜的种植方法推广,把章家痛心烧姜的事迹,那是传的神乎其神。还添油加醋说烧了姜,感动了老天,没多久就下雨了。
市面姜是多了起来,可是要买姜种啊,那就得认准了章家。不为别的,就为放心二字。
那姜种可比其他用途赚的多,章家在众多姜户里头,还是杀出重围。
只要提到姜的,只要种姜的就没有不知道章家的。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这会儿大黄村进来了一个骡车,跳下来一个差吏和农事官。
那农事官就是崔卫风派来找章家记录生姜种植方法的。
许桂香沤肥的法子虽然有效,但是还不值得专门动用农事官。衙门里沤肥的法子自前朝就有,崔卫风正叫人研究。
而这因地制宜种姜的法子却只有章家做的最好,还得取经。
农事官没有品阶,是衙门里内部自己设置的考试,可以报名参加考试的都是祖祖辈辈和衙门有些关系的,这些书吏也相当于默认的世袭。
外来的官员语言不通,这便有很多地方需要本地书吏的地方了。话有歧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地方抱团的书吏能把县太爷耍成睁眼瞎。
衙门里关于崔卫风的评价多是愣头青,办事没分寸搞不了半年就会被拉下台的。
他们知道崔卫风没功名,那做派也不像是高官门第出来的,天天带着个木头护卫溜溜达达去钻小巷子找路边摊吃。只把崔卫风当做哪里的商贾砸了巨资捐了个七品县太爷当当。
这些书吏自诩文人傲骨,打骨子里就轻贱商贾白身,对崔卫风布置的任务心中多有埋怨。且崔卫风还夸了章家多有风骨,反倒惹得书吏看轻崔卫风,最后推来推去,推到一个家里种有生姜的书吏人身上。
毕竟下乡进村的差事捞不着油水,又是真的苦。
不说日头晒路颠簸累的半死,村里杂草泥土脏鞋面,跑去农家谁都不想喝一口水,农户一张嘴,露出黄牙污垢讲话和放屁一样臭。
这书吏姓姜,家里是耕读之家,早前章家卖姜时,他家就自己跑去外地学了种姜的手艺。可种出的姜,还没章家饱满个头大。
这会儿叫他来记录种姜方法,摆明是同僚们打脸他家,花了钱千里迢迢学还不如一个乡野村夫会种。
但同僚们不会这么明说,只说乡野风景甚好,叫他这个诗痴下乡找找灵感,别一天闷在工房里啄茶杯了。
那姜书吏酷爱做诗,可心想他也不是傻子,同僚看笑话他还是分的出来的。那流民村,穷乡僻壤灰扑扑的有什么可看。还庆幸没下雨,要是下雨一脚泥泞,心情更糟糕。
就是记录姜的法子,那就记录,就当再去交学费了。
只是一个种姜的法子能换二十亩地,这简直闻所未闻。
因为前朝亡于圈地,多地流民起义爆发,导致现在田土流转朝廷管理严苛,禁止土地买卖,力度之大强过历朝历代,以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上偏僻朝廷手伸不了那么长。
可现在上有驸马爷圈地被杀,下有县令发现乡绅土地买卖可做政绩,这风头上,谁敢买卖。
就是之前低贱买地的,朝廷都要乡绅官员把地退还。
那山狗村的二十亩田原本是被村长卖给地主了,后面那地主也被衙门要求退还田,至于钱,那迁走的十户人家早就到西北了,反正朝廷不补钱的。
地那么金贵,有钱都买不到。一个种姜的法子换二十亩地,这叫姜书吏如何不气愤。
他家当时去外地学了一年,脚费加食宿费加送礼买方子的钱,总的下来也只有五十两。
这章家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要二十亩地。
县令年轻没什么阅历,定是被人骗了,他可不是那些没经验的毛黄小子。虽然私底下不待见县令,但毕竟是县令,接了差事,姜书吏还想办个好,最好是直接降低成本。
得了县令的青睐,便让那些揶揄他的同僚吃个瘪。
那便先探探章家的虚实。
姜书吏先是问大黄村关于章家的情况。
好巧不巧,正好就碰到了黄家父子。那嘴里的话能有个好的?说章家心黑手狠,一村霸王蛮不讲理,还说章家压根不会种姜,那姜都坏死一亩田了。
姜书吏眉头紧皱,心想果然,被他抓住把柄了。
姜也生病了,和他家也没什么区别,哪里来的脸要二十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