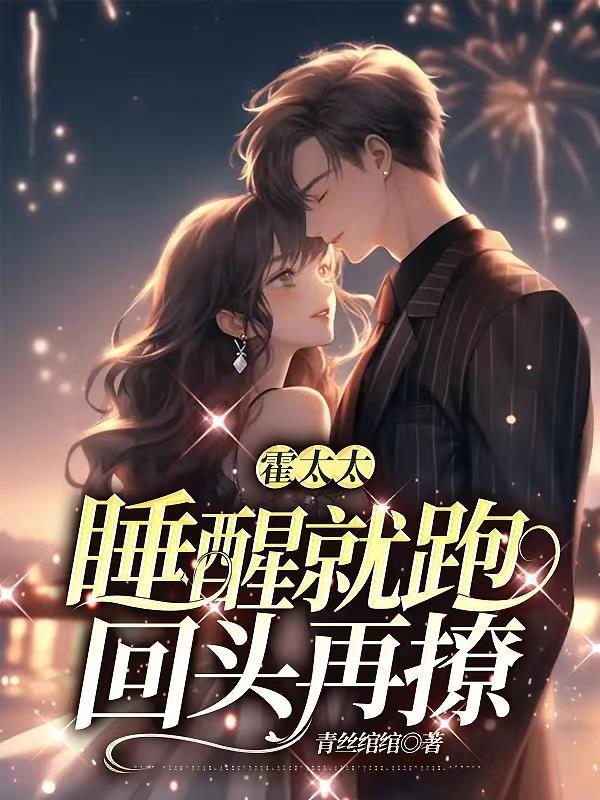新纳兰小说>天官纨绔枫香 > 第88章(第1页)
第88章(第1页)
赵王氏其实没想过,这么快就能把一套教科书编纂出来。
她一边校对,一边说道:“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不过可以先这么教着试试。后续再补充各地实际情况的内容。”
她通过各种方式调研了各行各业日常需要用到的词句,和赵淩一起,编纂了一套用于注音和断句等的符号。
现在字的发音都是反切,用两个字拼凑在一起,切上字取生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
这种方式在刚开始是不错的。
但语言是不断发展的。
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时代,会衍生出不同的发音和含义。
反切的局限性太大,不如注音符号更加规范、清晰。
这一点,在神都的官场上尤为明显。
官员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用的都是一套教材,但只要一开口,基本就能知道某某官员是哪里人。
甚至有官员因为口音重的问题,升迁受阻。
没办法,汇报的内容,皇帝听不懂,还得请个翻译。
譬如赵骅这样,皇帝经常要跟他单独说一些事情的,总不能得有个翻译在身边,缺乏保密性不说,也有可能转一手之后表达的意思有偏差。
和其他官员交流的时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而注音,只是基础教育中的基础部分。
赵王氏编纂了配套的字典,收录了常用字三千多个。
配套的教材并不厚,赵淩还给画了插图,通过简单的图画,将书中词句的应用场景进行表述,看起来更加清晰。
即便如此,他们调研的地方基本局限于神都,另外一部分来自于曾经外派的官员们所提供。
赵王氏对最后成型的薄薄四册教科书,并不算满意:“要是能亲自游历各地就好了。”
赵淩想也不想就说道:“娘,我带你去!”
话落,赵王氏和赵骅一左一右拍他后背上。
“尽给你娘画大饼。”
“你要带你娘去哪儿?”
赵淩感觉到赵王氏轻轻的力气,以及赵骅重重的巴掌,跳起来躲在赵王氏背后:“娘,你看看这个坏爹!”
“这个坏爹”想着大过年打儿子不好,懒得搭理他,在赵淩空出来的位置上坐下,帮着赵王氏一起校对。
赵淩瞧着夫妻俩,颇有点同桌的味道,慢吞吞坐到他们对面,画起了画。
大书房里,其他人各干各的事情,偶尔经过赵淩身边的时候,瞟一眼,再看看赵骅和赵王氏。
夫妻俩很专心,浑然未觉。
到了傍晚,赵喜过来叫人。
今天家中做了丰盛的席面,擅长跳舞的六姨娘和擅长弹曲的七姨娘泪眼婆娑地跟赵骅和赵王氏磕头:“多谢老爷夫人。”
赵王氏笑道:“好了,快起来吧。今日过后,你们就是我赵家的表姑娘,出去好好过活。咱们照旧是一家人,有什么难处,记得回家里说。”
两位姨娘又给赵王氏磕头。
哪怕进门已经有几年时间,两人的岁数也就二十上下,都是花一般的年纪。
她们进赵家的时候岁数还很小,懵懵懂懂地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七姨娘那会儿自觉自己很清楚,实际上在赵家待了几年,跟着当家主母学习了几年时间,才知道女子原来可以做这些事情,也可以做那些事情,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不是囿于后宅,当个……嗯,工具人。
赵王氏让丫鬟把两人扶到桌前坐下,眼中带着笑意:“好了好了,大喜的日子,不要哭。”
跟着两个姨娘身后,又有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妻带着两个孩子过来磕头。
赵王氏也笑着说了几句。
这是赵王氏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情——把一些仆役改为良籍,让他们更方便行事。
这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依附于赵家,成为赵家这棵大树扎往更深更广阔之处的根须。
只是以前她并没有安排姨娘出门,这还是第一次。
玉书坐在下首,看两名姨娘,心里面五味杂陈。
这两名姨娘以后就是赵家在外的一方管事,权力比一个小小姨娘可大多了,过日子也松快得多,能够自己当家做主,不用看人脸色。
由于神都置产困难且太过打眼,赵王氏这些年置产不得不越来越偏且零散。
这就加大了管理难度。
另外就是赵淩捣腾出新东西的速度太快,无论是店铺的数量还是生产的人手都得扩大。
这年头,培养一个读书人很难,培养一个合格的掌柜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