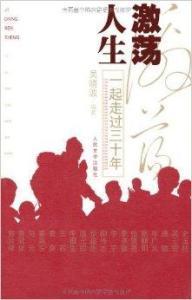新纳兰小说>樊青芳 > 第1章(第2页)
第1章(第2页)
除了出租的那栋楼,院子右侧还有套两层小楼。规模比起出租的那套小挺多,一楼是一间茶室,落地玻璃,亮堂通透。栾也在茶室里和对方签完合同。三个月短租,加上押金一共4800。
老太太从兜里翻出手机翻了个面,手机壳背后贴了个巨大的收款码,周围有点磨边了。
栾也把钱转过去,到账提示声音挺大,对方递了三把钥匙给栾也,其中一把是黄铜的,沉甸甸。
“两把你屋的钥匙,一把大门钥匙,大门不锁,你锁好自己房间。”
她指了指茶室的楼上,“我住这上面,房子有什么事情就找我,你和他们一样,叫我木阿奶。”
她顿了一下,语气挺严肃:“下午三点到五点不能找我,我要去打麻将。”
栾也被她搞得也严肃起来,特别郑重地点点头。
木阿奶接着说:“你的号码也给我一个。”
栾也愣了一下,没立刻开口,翻出手机点开SIM卡,把上面那串数字念了两遍。
木阿奶按照他念的号码拨了过来,等打通了又挂断,边存边问:“年纪轻轻,自己号码记不住啊?”
“嗯。”栾也点点头:“记性差。”
整个租房的过程太过迅速,等回到房间栾也脑子还有点晕——也可能是病的或者累的。
位置虽然偏远,但房间还是不错的。
头顶是三角形的吊顶,显得空间很高。房梁和柱子裸露在外,客厅里的茶几和书桌也全是木制。
卧室在左侧,没有和客厅明显的区分开,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地台。柱子两旁绑着纱帘,放下来的话勉强算作隔断。不过因为房间确实挺宽敞,也不显得拥挤。
卧室和客厅都朝东开了两个长方形的窗子,挺大,正对着雪山——栾也看了一眼,现在天气又阴了下去,外面是沉沉的云,遮住了山。
他把窗子全都打开透风,打量卧室里那张床。
床单被子都是白色的,酒店用的那种。栾也走过去仔细观察了一下,看起来没什么明显的污渍,但不确定铺多久了,毕竟租房不可能像酒店一样一天一换。
靠墙放着一个木衣柜,栾也打开看了一眼,空的。
栾也回到沙发上,又下意识掏出一支烟放进嘴里,才想起来自己的打火机留在机场安检了。
他干脆把自己唯一一个包打开,浑身上下所有东西都翻了出来,放在面前小小的木头茶几上。
身份证,护照,充电器,手机。
这是跑路必需品。
随手拿的z9相机和镜头,备用电池和充电器。
这是他的饭碗,也是他出门的理由。
出门拍几张照片,这个理由对他来说太充分了,充分到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足够让他从地球另一端悄无声息的消失,出现在西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
机场买的手机卡,全新到连他自己都没记住号码。
微信是新注册的,联系人列表里只有今天刚加的租房老板的儿子。
银行卡是很多年前回国时办的,几乎没用过。
非常好。
栾也关掉手机,重重倒在沙发上。
按道理他应该出去买点生活用品,牙刷牙膏,新床单被子什么的。或者出去吃个饭,过去30多个小时里他只吃过一次飞机餐。
栾也闭上眼。
太累了,先睡再说。
这应该是他这段时间来睡得最沉的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窗户外昏暗一片,不知道是几点。
风从窗外吹进来,窗帘晃晃悠悠。有点冷,栾也缓了一下才爬起来。
睡了一觉,感冒症状不减反增,他喉咙疼得厉害,下意识想要清一清嗓子。
一开口,栾也就知道完蛋了。
虽然之前自己嗓子哑得跟唐老鸭亲戚似的,但至少还能简单的说两句话。结果在沙发上对着窗户睡了一觉,不知道吹了几小时风,现在栾也居然彻底失声了。
他努力尝试着张开嘴啊了几声,只能感受到嗓子里微弱的气流经过,别说正常说话了,连一个音节都没能成功发出来。
这时候房间里没开灯,挺暗,他坐沙发上努力尝试发声的场景看起来挺心酸。
试了大概十秒,栾也果断放弃了。
去他的吧,反正自己现在是一个人,哑了正好,用不着和人说话。
他头发有些长,之前东奔西跑没时间去剪,干脆用皮筋在脑后扎起来。睡了一觉有点散了,栾也用手随意拢了两下重新扎好,拿起手机出门下楼。
院子里没人,只有两三盏地灯昏昏暗暗的亮着。穿过院子走到门口,大门是农村很常见的木头门,朝里挂了一把大锁,确实没锁,虚掩着,一推就开。
他得出门买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