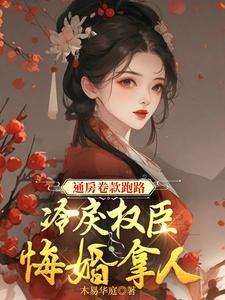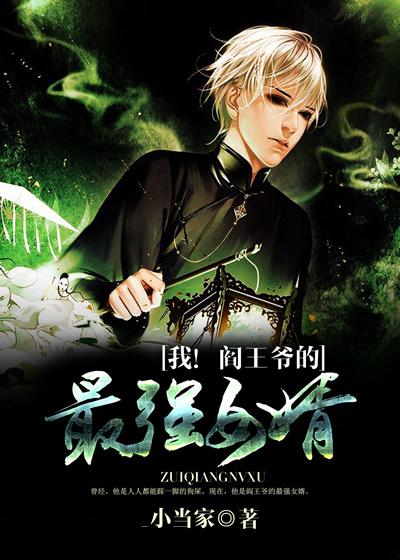新纳兰小说>内心戏被反派知道后免费阅读 > 第56章 是恶是善(第2页)
第56章 是恶是善(第2页)
段怀瑾当不成无情无义的“神”,因为他只是个会赌气、会愤怒、会害羞、会恶作剧、会想牵爱人的手、会想家人永远健康、会想和朋友永远保持友谊、会想所有人都能获得好结局的人类。
他知道自己有时的内心想法很阴暗,可是只要拥有情感的人类,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烦恼。
段怀瑾不将这些阴暗的想法表现出来,拥有这样的想法,并不邪恶。
可将这样的想法付诸行动,那就是罪恶。
而齐月白和顾望飞,就是将自己的阴暗想法变成现实的人。
有人喜欢谈论善恶,总是将善恶当成一种标签。
只要一个人被打上善的标签,那他一定就是个从未做过坏事、没有任何阴暗想法、单纯善良的好人。
而当一个人被打上恶的标签,那他一定就是个一生做尽坏事、没有任何善意举动、凶残狠毒的恶人。
可人是无法单纯被贴上某一种标签的,没有极致的黑与白,只有中间值的灰色。
顾望飞虽然恶贯满盈、罄竹难书,可他依旧实打实资助过贫困学生。
哪怕他只是为挣个好名声,可对于被资助的贫困学生来说,他就是资助自己的“善人”。
齐月白同样做过不少坏事,可还是有不少人都相信他,甚至将他捧上神坛。
如果他没有在众人面前装出好人样,做那些善事来迷惑众人,大家也不会这么追捧他。
段怀瑾不想去评判什么,在这个被剧情控制的世界里,谁都会成为下一个炮灰,因为他们要为主角开道。
可主角又何尝不是被剧情控制,被套在预设的模板中,按照他人的想法生活下去。
段怀瑾没什么兔死狐悲的想法,如果他真的有,那他就是下一个罪大恶极的顾望飞。
他只是觉得讽刺罢了,他人的生命,不过纸上零星两字,他人的前途,不过随口一提。
在这个失去自由的世界中,没有谁是无辜的,也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
因为剧情只会控制主要部分,一些细节根本不会被控制,这不过是他们在欲望驱使下做的。
没人逼着齐月白去杀人,因为书中写那是顾望飞做的,可实际杀人的却是齐月白。
剧情没有逼他戴上一张恶心的假面,也没有逼顾望飞去打压那些小公司,这一切都是在他们自我意识驱动下导致的。
苏瑜记得小说中有写,齐月白有个习惯,他有一个带锁的木盒,那是他的母亲在童年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个开过光的木盒。
而盒子里,放满了齐月白的忏悔,木盒一直被他埋在老家别墅里的树下,没有他人知晓。
小说里还特地强调,齐月白在盒子里装着他做过的坏事和所做坏事的证据,可几十年过去了,盒子里居然只有零星几张忏悔纸条,可见他有多么善良,一辈子都几乎没有做过坏事。
齐月白要怪只能怪小说,都怪小说里把他的习惯写得太过详细,才会给苏瑜可乘之机。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警方从齐月白家里挖出木盒后,里面满满当当的纸条上记载着一个又一个的恶行。
好家伙,从辱骂欺凌同学、夺走他人论文、开除排挤下属、到杀死“徐卫”,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受害者的名字都一清二楚,甚至连证据都完美陈列在其中。
果然是小说设定啊,小说为凸显齐月白的善良而给出的设定,最后却成为最利落的一刀,直接将齐月白的假面斩断。
聪明人怎么能留下犯罪的证据呢?
要论忏悔,干脆直接在心里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过,然后掉几滴眼泪,最后就可以当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才是做下这些坏事的人会做的事。
木盒被挖出后,齐月白的表情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如此鲜活,如此生动,如此的真实,完全将人类所有卑劣的欲望都尽数展现出来。
齐月白在被抓走前,苏瑜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忏悔纸条?
他冷着一张脸,却还是带着一些骄傲地说:“那不是忏悔,是记录,我做的又不是错事,为什么我要忏悔?”
苏瑜被他噎了一下,的确,齐月白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错事,当然不会忏悔,不过是小说设定罢了。
几秒后,苏瑜又接着问:“那为什么要留下这些你做事的证据?”
齐月白仿佛一道完美的程序,也按照设定说出那句:“我就该这样做,就像你们都应该喜欢我一样理所当然。”
主角光环可以把他捧得高高的,但同样,他也会被主角光环所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