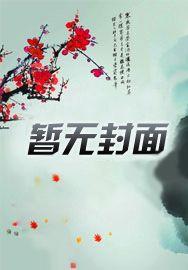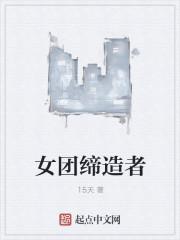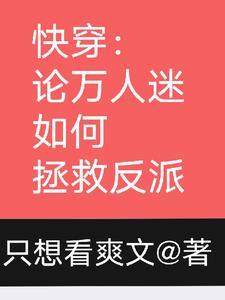新纳兰小说>我爹张居正!不早八的方糖 > 第11章 说书人喜欢断章(第2页)
第11章 说书人喜欢断章(第2页)
而是指洪武年间,朱元璋御封的三十九匹运送官茶的马。
后来随着往来行商,城内便出现了这一家以“三十九铺”为名的茶馆,算是如今京城内人流往来最为密集的地方。
城内的不少中下层文人,下了工的京城百姓,都喜欢进入茶楼点上一盏茶水,几样小菜,跟三五好友一齐,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听茶馆内的“柳先生”说书。
今日柳先生来得有些晚了,底下人等得有些焦躁。
“柳先生呢?快让他出来!”
“咱们这茶钱可是为柳先生而来!”
“水泊梁山的故事说到哪里了?宋公明是否受了诏安?”
。。。。。。
直到茶馆里头怨声载道,穿着一席道袍,留着山羊胡子的柳先生才不疾不徐地走出来。
他登上木质高台,握紧手中醒木,“啪”地一声重重拍下,声音脆响。
茶馆里的嘈杂声顿时消失不见。
柳先生的清朗且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发出:“列位看官,今日咱们不说水泊梁山。。。。。。”
此话一出,台下顿时就有不少看客离席了,老子就是来看这的,你竟然不讲了?
柳先生丝毫没被离开的人所影响,面容淡定地说道:“水泊梁山的故事反反复复说腻了,今日得了一个新故事,乃是源自武周年间宰相狄仁杰狄公的话本。。。。。。”
明朝时,说书人、娼优、杂耍等被称为“下九流”。
这种不入流的职业,在许多士大夫看起来,跟街头老鼠没有什么分别。
到了明中后期,市民阶层壮大,许多在城中帮工的百姓,有了一些闲钱,出入茶馆、勾栏等娱乐场所。
有人追捧,说书这个行当便兴盛起来。
柳先生原名柳静亭,南直隶扬州府人士,他自小浪迹在市井之间,读过几天私塾,对于小说、话本有着狂热的爱好。
这几年,他游历大江南北,终究在京城首善之地落脚。
柳先生的说书简洁干净,也不唠叨,说到细致入微之处,叱咤叫喊,十分生动形象。
这便是他看家的本领。
“话说唐高宗龙朔年间,大唐与新罗联手于白江口击溃百济与倭国联军,百济女子玉素被掳回大唐,从此流落风尘。。。。。。《黄金案》就此发生。。。。。。”
柳先生的声音沙哑,一下子就勾起了茶客们的好奇心。
当然,面对一个全新的故事,有人激动万分,也有人嗤之以鼻。
如坐在楼上雅间的两位茶客。
“老朱,这《大唐狄公案》你觉得如何?”
面容瘦削,一看就是纵欲过度的公子哥,扭头与身旁友人说话。
“哼!”名为朱应槐的少年人,身材矮胖,啃着烧鸡说道。“无趣,又是什么小家子气的公案,那些穷酸读书人写出来的话本,还不如我从刑部拿来的案宗有趣!”
说话间,朱应槐撕下一只鸡腿,递了过去说道:“呐~张元昊你要不要来一只?”
直呼名讳很粗鄙,可瘦削公子哥习惯了。
他压低声音:“小声些说话,你我二人出来一趟不容易,若被些言官发现了,定然又要告御状了,届时老爹又要罚我们了。”
“言官?”年龄不过十六的朱应槐轻笑。“他们不会理我们的,他们撺掇着想搞张居正呢,哪有功夫搞咱们啊?”
不愿提朝堂之事,张元昊瞥了一眼台下的“柳先生”,正说得慷慨激昂呢。
听着什么“狄公上任蓬莱县令”“前任县令横死”“县衙主簿失踪”。。。。。。。他只觉得小家子气,一点都生不起兴趣。
他二人是靖难功臣的后代,朱应槐出自朱能一脉,张元昊出自张玉一脉。
两人年纪相仿,又有着差不多的家世,还都不是家中嫡长子,平日里无事,便时常在京城内厮混。
听书,乃是二人最为热衷的娱乐活动之一。